1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一直致力于国际问题的教学与研究,见证了许多令人难忘的瞬间。在这段时光里,有一些让我铭记终生的“第一次”经历,它们不仅充实了我的教育生涯,也为我的研究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首次踏足国际论坛,我深刻感受到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那是一个充满异国风情的场合,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们分享观点,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这次经历让我明白,国际问题不仅仅是理论的探讨,更是文化、历史、与全球共同关切的未来的交汇点。
第一次亲身参与国际合作研究项目,让我感受到团队协作的力量。在与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伙伴共同努力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尊重与包容的重要性。这次经历激发了我更深层次的思考,认识到解决全球性问题需要跨越国界的合作,而这正是学术界的责任与使命。
首次在国际舞台上发表个人研究成果,是我职业生涯中的又一重要时刻。那一刻,我感受到了知识传递的力量,也意识到每一位研究者都有责任为社会进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次经历激发了我对教育事业的热情,让我坚信教育是改变世界的关键。
回顾这些“第一次”,我深感幸运能在国际问题领域有所建树。这些经历不仅是我的个人成长历程,也见证了国际事务发展的巨大变革。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坚守初心,为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而努力奋斗,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际问题的教学与研究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近半个世纪的探索历程不仅耗费了成千上万参与者的心力,还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故事。在沧桑变革的浪潮中,个人的亲身经历如同大海中的一滴雪泥,或许微不足道,却可能有助于揭示其中的机理,留下独特的印记。"
"1. 1982年,北京大学举办的首次国际政治讲习班"
1982年底,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举办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届国际政治讲习班。作为当时刚刚留校工作的一名年轻教师,我怀抱着一份迫切的心愿,渴望在我们大学系统内系统推动国际关系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前辈老师们的理解和支持,前往这个讲习班成为我在校工作后的首次学术出差。
回想当时的情景,1982年底的北京已是严寒初冬,然而,来自各地各部门的百余名学员都怀着满腔热情投身到这个文革后的首个相当系统且高水平的国际政治专业培训中。整个讲习班历时一个月,北大国际政治系的系主任梁守德教授及其他核心教师们倾心努力,致力于办好国内第一届国际政治专业讲习班。
在这个讲习班中,授课教员的阵容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不仅有外交部副部长宫达非、中调部领导陈忠经、外交家冀朝铸、学术权威陈乐民,还包括资深外交官、英语专家薛谋洪等一批当时最杰出的专业外交干部。这个经历让我深受启发,成为我学术生涯中的重要起点。
记得那时,北大校园仍保持着改建之前的古老风貌,尤其在隆冬时节,校园在寒假中显得有些冷清。某个下午,宫达非副部长亲自上阵授课。据我了解,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北大讲课。一走上讲坛,他环顾四周的教室,开场白竟然是:“看来,北大的校舍比有些非洲国家的还差劲。”这一番话引发了全场的一阵感慨。
陈忠经则深入探讨了台湾问题。身为高级主管干部,他不仅毫无官腔,甚至带有一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古朴风范。在讲述当时台湾名记者江南被刺杀的案例时,他的叙述既引人入胜又深刻透辟,特别是对该事件的分析更是精准到位,至今回味犹新。
薛谋洪大使身为资深外交官,曾被中央委派专门负责整理新中国外交档案文献。因此,他的讲课不仅展示了他曾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担任中方高级英文翻译的风采,还首次向我们传达了这位战争亲历者通过档案文献系统研究所得的新观点:“朝鲜战争的结局是中美打成了平手。”
然而,这次讲习班对我影响最深的是陈乐民先生的两堂课。他早上讲授欧洲问题,下午则深入探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整个讲习班中,陈先生是唯一一位独自承担两次讲课的专家。他引用戴高乐的一句话给学员留下深刻印象:“当莎士比亚还讲英语,巴尔扎克还讲法语,但丁还讲意大利语,那么,欧洲就还是民族国家的欧洲。”亲历了半个世纪以来欧洲剧变的我们,不禁为前辈学者的深远洞察而感慨。
"回顾四十余年,我参与了无数次国内外专业讲习班,也主持了无数次各种各样的培训活动。然而,最难以忘怀的经历,甚至到今天仍保存着整整一个月的讲课记录的,莫过于1982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那次国际政治讲习班。"
"2. 1982年的首堂教学实习课——《共产党宣言》"
按照学校的传统,青年教师留校后需要通过实习课的考核。而我选择的实习课内容是《共产党宣言》。尽管当时对这部经典著作的理解无法与几十年后的积累相提并论,但我清晰地记得,通过反复阅读,两位经典作家所表达的深刻历史洞察和强烈的思辨逻辑当时震撼了我。
在讲课中,我一方面着重强调《宣言》所描绘的共产党人的宏伟理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另一方面,我特别强调了“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是需要历史条件的”这一思想。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宣言》历次序言中反复强调的:“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但是,《宣言》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要“更透彻地了解工人阶级解放的真正的条件”。而理解这一条件的关键在于:“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 只有当大规模生产得到充分发展、只有当被压迫阶级的意识超越手工作坊与教堂的尖顶,只有当“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时候,被统治阶级的真正解放才是可能的。
那时,我的助教辅导老师是周尚文老师。周老师聆听了我的这堂课,一边热情地鼓励,一边又以严格的标准要求我进一步系统化对《宣言》的理解。这番教诲一直伴随着我几十年的教研生涯。
"3. 1987年的首次东西方比较国际考察"
对国际事务的认知,不仅需要读万卷书,还需要行万里路。80年代,我有幸在留学生涯中获得了一次宝贵的机会。在1986到87年间,在苏联学习的最后阶段,经过使馆教育处批准,我从苏联出发,向西行至波兰,再进入德国。我穿越了东柏林的柏林墙,到达西柏林,然后南下奥地利,途经近在咫尺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经过布拉格,转向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然后经过乌克兰的基辅,最终东返苏联本土。整整一个月的行程中,我亲身目睹了仍然处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苏联和东欧各国,包括当时波罗的海三国在苏联境内的地位。尽管这是在冷战终结前的最后时刻,但改革的风潮已经兴起。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显示出了变革的迹象,尽管社会仍然相对稳定。
在此次考察中,由于与新华社资深记者同行,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能在各地的新华社住宿,省去了大量的费用。更难得的是,我有机会聆听到驻各国新华社老记者们对当地历史文化以及冷战末期形势的周详而深刻的介绍。这次经历使我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社会变革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这次旅行最令人难忘的,莫过于在行走的过程中对“东西方文明结合部”这一学术概念的深刻领悟。在欧亚大陆的西端与东端之间,存在着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片“东西方文明结合部”。从人种的角度看,斯拉夫人、日耳曼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犹太人、高加索和中亚各地的人等在这里交汇。从宗教的角度看,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各种力量在这里交织。从自然地貌来看,从东欧大平原向西,逐渐进入中欧与西欧之间的森林地带,向南则是丘陵与山地。而从人文景观的角度来看,在苏联境内的莫斯科、明斯克一带,根本无法看到那种西欧风格的、以所谓“市民社会”设施——比如市政厅、商会、教堂、法院、广场、老街——所组成的“老城区”。然而,从华沙老城向西,逐渐展现了更加西欧风格的氛围。维也纳更是如此。
当时的考察虽未到达伦敦与巴黎,但仅仅从东柏林阴郁的地铁里曲曲弯弯地爬升,穿越柏林墙,在五光十色的西柏林“裤裆大街”(Ku’damm)一览无余,那里的风俗与政治的开放程度,与莫斯科相比,让人感受到天壤之别。在东方与西方之间这片错综复杂的区域,从我对“文明结合部”的初次体验开始,一直伴随着我这一生的国际交流与研究。
"4. 我的首部合著专著:《国际风云的产儿》"
苏联归国后,在倪世雄和金应忠两位老师的邀请下,我有幸参与撰写了我一生中的第一本合著专著《国际风云的产儿》。该书于1989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或许是当时国内最早介绍国外国际关系理论的著作之一。倪老师负责撰写美国部分,我负责苏联部分,而老金则负责中国部分。当时浙江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对此书的写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她深刻地感受到了我们写作的认真和深度。
实际上,我在苏联访学时有两个目的:一是系统研习俄国历史,二是完整了解苏联国际关系思想与理论。就后者而言,我带回来的几十种相关著作相当全面地反映了苏联晚期国际研究的面貌。值得一提的是,60-80年代苏联学者对西方国际理论曾进行过非常地道的译介,但每一种译作的封面总会加上一句“批判性地介绍西方理论”,估计是当时意识形态管理的背景下作者的“防身之用”。与此相关,到了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却没有出现过类似于我们国内普遍宣扬“三大主义”(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的现象。也许是因为二十年前早已有所接触,所以那并没有显得那么新奇。因此,我仍然认为对于从苏联到俄罗斯的这一过渡时期的国际思想理论,包括众多西方国际思想与理论,我们仍值得花时间深入研究。当然,以今天的视角来看,我们需要在全新的语境下对其进行诠释,这也包括像华为总裁任正非所持的态度:通过向对手学习,探索化解压力的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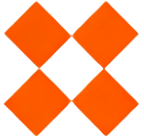 新起点 超级网址导航
新起点 超级网址导航
